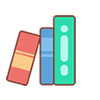恆的五行属性是什么?
“恒”字,《说文》解作“亘”,其言曰:“亘,常也。从辵(音chuò)亘声。”“亘”者,《康熙字典》解释为:“直延貌。”“常”者,《康熙字典》解释为“不出异常。” 由是观之,“恒”的意思也就是一直持续下去的状态,这个状态是静止的、是不变的。
《论语·子罕》记载孔子的话: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,从我者其由与!”意思是我如果真的一辈子都没法实现自己的理想,那我只有坐船到海上隐居了。我的弟子中恐怕只有由了吧!由,就是子路啊。这里孔子自比为伯夷,以山行海走象征自己坚守正道,无所通达。子路在,故有“乘桴浮于海”的念头;子路死,遂绝此念。可见孔子的思想是有进境的,他年轻的时候想的是入世,中年的时候想的是“中庸”,老来则追求“德治”和“礼乐”,其实这些都是“恒”的体现——一个“志于学”的人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产生,这是正常的。但是,如果一个人到了这种程度还不断进取就不正常了,这就超越了“恒”的范围,老子称之为“敝兮”,庄子称之为“弊足”。
在《论语·子罕》里,当孔子自我感慨要“乘桴浮于海”的时候,子贡就说他不“志于学”了。同样,在《论语·先进》篇里,当子路问如何才是君子的时候,孔子也说他要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才能做到像他自己一样。这其实就是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不要陷入自我的执念之中。否则,就像《庄子·秋水》里面说的那样:“夏虫不可以语于冰。” 当然,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觉悟而只是受外在约束而被动地遵守规矩,那就会像机械一样僵硬死板,那就不是自然之道了。所以古人说,要在遵守规矩和不违背本性之间做到张弛有度、平衡调和。这就是“中庸”。
恆字的起源
“恒”是一个会意字。甲骨文字形由月、心和二组成。徐灏在《说文注笺》里注的很明白:“恒者,月之恒星,犹言恒星也。星以月行为正,故从月;心者,人心见(现)象于天,盖星所附丽而行者,从心,以着附丽不贰也;二,数之至,言星行循轨常也”。“恒”本写作“恆”。本义是“恒星”:固定不动的星辰(相对于“行星”而言)。《说文》:“恆,月之从星,与心、肾同。”段玉裁注:“言从月而出入者,心之一名恒星,是之谓恒,谓其固定不动也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观阴阳之开塞,以候天地之诚,实也。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(冥)事物者也。言尽于名,而不名于命(冥);名尽于言,故曰,‘天地之大,亡(无)大小,万物各以顺名定类。’此其所受于天也。故昔之所论列,是上合于天(冥),下设于地,中顺于民心,参(叁)于孔子之论,可谓要矣,此言至要也。书缺简脱,礼坏乐崩,圣人作而后可以正,今论先王之道以为元首,欲令乡(向)学者有所折中。故曰:帝王之学也,非天下之至德,其孰能与于此。盖闻文王之时太平,辞不及已(己),周公、子赣之徒美而成之。孔子不有大德,何能若是。故曰:‘不有至德,至于神明,其孰能与于此。’今游谈者,不好学问,以为文事关儒术,必先诵庄、老子,而击訾文章。言庄、老则入节,诵五经则鄙野,此乱道之士也。盖不喜诸子,则去《易》远矣;去《诗》、《书》则不论礼乐焉;去《礼》、《乐》、则无以行,无以将矣;去《论语》则无君臣矣;非孝道则得罪于人。五者俱废,君子安为哉!故诸子者,疑圣人之作也,其言虽浅,必有取焉。若庄、子亦云:‘升苍天,杳焉乃去;奔黄河,泛焉不还。’庄、子之游,意亦远矣。”
恆字的五行属水。